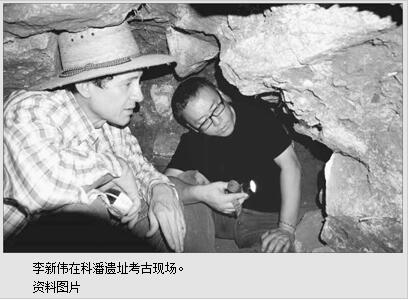中国考古,走出国门探源世界文明(文化脉动)
本报记者 郑海鸥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科潘遗址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他们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而中国却对玛雅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据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基础研究。”李新伟说,我们主动走出去,将极大地改变这些状况。“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考古大国,我们不满足于只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际舞台,也渴望成为世界考古强国、文化强国。”
凭借务实态度和责任感,“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队,没让国内外的关注者们失望,一连串惊喜随之而来。
2010年到2013年间,北大考古队先后4次对肯尼亚的5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还对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三次调研。
“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带队去肯尼亚考古,他说:“陶瓷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但让中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世界贸易史、航海史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使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商业生命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14年5月,王建新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山前地带开展的春季考古调查工作结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马尔罕市内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托蒂,托蒂带领的团队当时已在撒马尔罕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5年了。
“听说我们也在这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们,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调查了15年了,你们还调查什么?你们会调查吗?’当天下午,我们在考古研究所汇报了我们本季度调查工作的主要收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汇报会。当托蒂了解到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他们已调查过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遗址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立即想要与我们谈合作。”王建新感慨,通过务实努力,我们在古代游牧考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才能得到外国考古学大腕的尊敬。
科潘遗址发掘也不乏让哈佛大学的专家们眼前一亮的惊喜出现。“玛雅人相信万物都有生有灭,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到一个时期,就会把之前的建筑推倒,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建筑。于是累积起来,不同时期的建筑最终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李新伟说,中国考古队在发掘时通过“解剖”,发现了至少三个时期的建筑,这为了解科潘王国的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对居址东部进行了发掘,但他们并没有对居址进行深入解剖,我们算是填补了他们工作的一个空白。”
王建新团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很多探方挖掘后甚至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许多国家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终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负责任的考古态度。我们不仅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还进行了实地保护,有的建了展示大厅,将来将建起小型的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队的这些“靠谱”行为,受到了普遍赞誉。
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是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无力保护,现在终于有实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认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这让考古专家们自豪和振奋。
“在科潘的整个工作过程比预想的都要顺利!比如,我们担心当地政府可能并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权威学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帮助我们。实际开展工作之后,感受最大的就是来自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帮助。”李新伟感叹,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大家相信中国能做好一切事情。”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境外考古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农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种区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还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王建新指出,欧美、日韩各国纷纷将海外考古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项目的持续开展,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加深了他们对这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秦大树也举了个例子,“肯尼亚陆上考古成就令当地学者和民众为之兴奋,他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感到骄傲,也为找到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感到高兴——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比英国学者之前认定的14世纪向前推进了四五个世纪;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纪,表明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商品就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发掘出的永乐官窑瓷器,基本确定了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现在我国的境外考古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采访中,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明的知识储备、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都还不够充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还欠缺,要想进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争取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依旧任重道远。
王建新展望,预计经过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考古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取得话语权,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研究的主导权。“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世界考古学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4日 19 版)